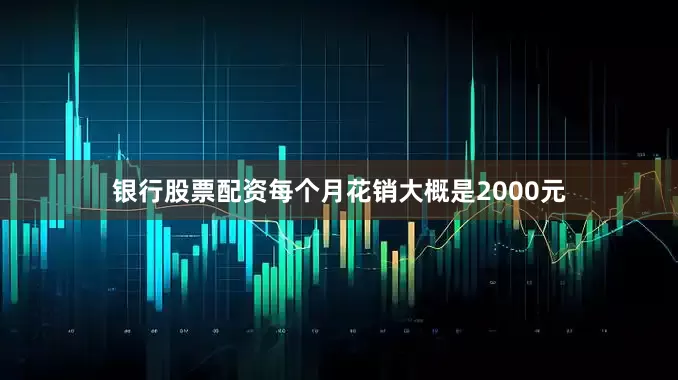今秋九月
大工外国语学院将迎来办学四十周年纪念庆典
四十年来,一代代外语青年书声琅琅
化作学院桃李芬芳的不辍弦歌
一届届外语学子并肩前行
铸就学院赓续发展的坚固基石
值此欢庆之际
母校诚邀各位校友再叙青春,回家看看!
为庆祝学院办学四十周年
外院校友将自己与大工的点滴
落于笔端,铺陈为文
让我们一起品读!
作者简介:
展开剩余89%王一哲
外国语学院2014级校友
2014年-2018年:
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
2018年-2021年:
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国际新闻专业
现为:
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闻中心记者
我家在大连,高中就读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高级中学(现校友交流中心旧址)。高中和大连理工大学一小水沟之隔。
2014年的夏天,我最渴望的事儿就是离开家,去北京。还记得高考前,复习外的无聊时光,和同学折纸飞机,从教学楼上使劲儿扔出去,飞跃小水沟落在大工校园里。高考结束,想象在18岁的年纪飞越大江大河,结果只飞过一条水沟。
英语不是我的第一志愿,准确地说是最后一个志愿。11年前张雪峰恐怕还在创业,但各类专业分析的氛围也很浓。“语言不是一个专业”“英语谁不会”这些观点当时就很流行,再加上我妈妈大学就是英语专业,我想换个路子。命运弄人,我被英语专业录取了。
(最爱大工的玉兰花)
就这样,我开始了在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习。10年前的记忆已有些模糊,但入学之后有几点改观我印象很深。一个是,会英语和英语好不是一回事儿;另个是,语言是一种政治,读懂它所组成的知识文化、意识形态,本身就是个学问。
在某些方面,选专业如选爱人,经济适用重要,能让你得到成长更重要,若有“爱情”,那就是最幸运的事儿。没成想,我就是如此幸运!入学后,开始了密集的专业课学习,一道课题摆在面前:当我们整日不是为了一纸试卷而学,该怎样学习?当时没有意识到,这是多么幸福的课题——有时间和空间不功利地学习,这种好事儿恐怕人生难有几回。
阅读,大量、深度阅读。综合英语精读,词汇学,交替传译,同声传译等等,怎么学好呢?“看剧”不失为一种愉快方法,但所有语言学习恐怕都指向一个最朴素的方法:阅读。记得学院办了场交流会,一位学长说他最后悔的事儿就是在校期间没有多看书。我也听劝,英国文学课学了毛姆,就开始一本本看他的书,我通常在第一页写上我在哪儿开始看的,在最后一页写上在哪看完的,特有成就感。像这本《面纱》,我就是在一教开始看的,在宿舍看完。
(阅读仪式感)
借书,也有趣味。词汇学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本书Norman Lewis的《Word Power Made Easy》,这本书就像告诉你汉字为什么是这个偏旁,会的什么的意。这本书能买到精装,但我在令希图书馆借到了一个1978年的老古董,最早的借阅日期是1992年,看着还能发现前辈的幽默随笔。阅读对我们这代刷短视频的人来说不容易,给自己找点乐子,看下去就有改变。
(在图书馆借到的老古董)
张开嘴,读书或表达。学语言,“说”是个门面,不张嘴是不行的。先找差距,知道好的是什么样。榜样不难找,班上同学就有外国语高中上来的,一张嘴就不一样,羡慕得很。教我们同声传译的张睿老师,一口优雅的英音,促使我下决心改英音。当时和室友约好,比早课提前一个多小时起床,既能吃到沁园餐厅的土豆饼儿,又能在上课前早读。至于读什么,完全按喜好,大声读,直到读完。至于某句话,某段读没读懂不重要,重要是读。仝益民老师也教给我们一个好方法,就是用英语自言自语,插着耳机边走边说,说说自己的一天,要去哪里吃饭啊,好不好吃呀,胡言乱语就行,我现在还在做,挺解压的。
后来应该是在丁蔓老师建议下,我们找到在大工的国际生结伴,他们想学汉语,我们想学英语。我的伴是个菲律宾小伙儿,他是语言学博士,会多国语言。我们说一小时汉语,说一小时英语。他问我的问题,经常让我对汉语有新的认识。他的一个问题我后来问过好多人,“掉地上了”和“掉地下了”,字完全是反的,表达的怎么是一个意思?其实,对于翻译来说,汉语素养很重要。如果对母语都没有深入的理解、驾驭,怎么翻译?这也对我后来学习国际传播有启示,如果对自己的文化历史都不懂,传播什么?讲什么故事?总而言之,万事要有研究精神,不懂的、以为自己懂的,都有研究的余地。
(令希图书馆)
写作,外院的学习让我有很大提高。David是我们大三的写作外教,是一位美国大叔,记得还有一位新西兰女外教老师,很严厉。David教的是规范性写作,就像议论文,有几个观点句,分别给出论据,行文中丰富表达方式。他在交流中真诚地指出我的问题,语音是英音,但是说的话还是很美式,其实就是肚里没那么多“雅词儿”。后来,英音变成爱好,还是说美国方言吧!David期末给了我令人惊讶的:99分,估计把我的学习态度也考虑在内,大力拉升我惨淡的绩点。新西兰外教则鼓励我们随便写,像写日记一样不必给谁看,不必让谁看懂,天马行空地写,语法、outline统统不管,这个过程练习的是用英语思考,把脑子里的自我对话变成英语。毕业论文的写作,也让我们的英文写作水平冲上一个小高峰,感谢我的论文指导教师马泽军老师,经常不辞辛劳给我发来大段修改意见!
(马老师:努力了就会有收获!)
其实还有许多外院的老师,他们非常有人格魅力,和他们的接触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憧憬。院长陈宏俊教授,我有幸参与了他的大创项目,感受了一把真正的科研。二外日语的林老师,每次上他的课都很开心。我在校时,石田隆至教授还在大工外院日语系任教,虽然没上过他的课却总偷拍他,害,真是太帅啦!他是研究日本战争认知的学者,最近在新闻看到他受邀参加了阅兵式。当然,还有当时的辅导员秦志强老师,我在校参与了不少学生工作、党支部工作,他对我的影响可就太大啦!
(石田桑在1949coffee)
我之后的深造和工作,与外院的羁绊仍在继续。最大的羁绊就是,我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,当初不愿意作为专业的“英语”让我走得更远。工作后,作为记者,很幸运我的专业能在一些涉外场合派上用场。领导信任,我还专访了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裴国良、图灵奖得主霍普克洛夫特等人。
(专访裴国良海报)
2022年,“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”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让我想到我大一的班主任,温柔可爱的姜欣老师一直致力于茶典籍英译工作。事实上,典籍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就在大工外院,前身是典籍英译研究所,首任所长是著名翻译家汪榕培教授。我立即联系了姜老师接受我的采访,新闻在我台一频道播出。希望观众看到语言作为媒介的力量,小到日常沟通,大到让民族优秀文化站在世界之巅。
(采访姜欣老师有关茶典籍的新闻)
这篇回忆写到这里已经太长。其实和我同级、上下级的优秀校友太多了,都是人群中的佼佼者,我实在不上数,也实在没资格长篇大论。可能我更有资格说说自己的感悟,并不是做“最成功”的才有意义,做生活的“有心人”,也能成就一个最好的自己。
史铁生《务虚笔记》中说“如果你站在童年的位置瞻望未来,你会说你前途未卜,你会说你前途无量;但要是你站在终点看你生命的轨迹,你看到的只有一条路,你就只能看到一条命定之路。不知道命运是什么,才知道什么是命运。”
人生可以慢慢来,珍惜“未知的命运”吧!回想18岁,我走过的那条水沟,到达的已是一个了不起的高度,遇到的是了不起的人和事儿,这些成为了我永远的精神坐标。而那些大江大河,只要你勇敢地、坚实地踏上脚下的路,终究会到达。翻越山丘,还有下一个山海,路上风景,才是美丽的人生。
发布于:北京市加杠杆炒股的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正规炒股杠杆平台其堪称音响界的劳斯莱斯
- 下一篇:没有了